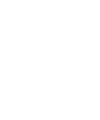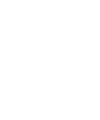离岛的人 - 离岛的人 第74节
全部都想起来了吗?
那他还会走吗?走了还会回来吗?
明明应该高兴的,可先从应春和身体里冒出来的却是恐慌。
时至今日,应春和也不得不承认在对待任惟有关的事上,他始终是悲观的、不自信的。
在任惟突如其来地出现在离岛,不打招呼就再次进入他生活的这段时日里,应春和时常会恍惚,总觉得如今的一切都像是一场过于美好的幻梦,是他偷来的。
他仿若是点燃了童话里小女孩的一根火柴,在梦里与任惟再次相见、再次相爱,一旦火柴燃尽,他就会从这场虚幻的美梦中醒来,回到没有任惟的寒冬。
一滴水顺着应春和的颈侧往下滑,温热的,有别于冷凉的海水,令应春和晃了晃神,后知后觉才意识到那是任惟的泪水。
任惟抱着他,十指扣紧他的腰与背,湿答答的手臂像两条自海底伸出来的水草,丝丝缕缕缠绕在他的身躯上,一圈圈绕紧,用力到让人难以喘息,好似溺毙。
可是在这样接近窒息的瞬间,也感到无限的安全感,被抱紧,被需要,被依存。
近在咫尺的声音恍若是自深海传来的海妖歌声,蛊惑着人就此沉沦。
“应春和,我爱你。”
“一直都爱你。”
长久以来,应春和都认为自己爱人的能力极度匮乏,在任惟身上一朝倾覆,过度透支,分手之后更是所剩零星,再经不起任何风雨。
应春和执拗好强,不愿承认是栽在任惟身上了,顶多承认任惟对他确有某种奇妙的魔力,让他原以为已然干涸枯败的心能再度复苏、再度泛滥。
他如同玩命的赌徒般不知悔改,倾家荡产过一次仍心有不甘,拿上所有的筹码豪赌一场。
他素来运气不佳,这次却得人偏袒,有心助他赢得头奖,想输也难。
有风吹过,熄灭了他点的火柴,孤寂暗沉的海面却为他升起一盏恒久明亮的灯。
胸腔里那颗惴惴不安的心也在这盏灯映下的暖调光晕里,自飘摇中落于实处。
可能运气这东西也存在守恒定律,在此处得了太多好运,就会在别处换回去。还没等应春和与刚找回记忆的任惟共度几日时光,任惟离开的进程就被迫提前。
这天两人一起吃早餐时,任惟接到了家里的电话,内容与四年前那通电话所差无几,连电话的背景音都来自同一家医院,堪称戏剧。
任惟挂断电话后,简单转述了电话内容给应春和听。应春和听完后,下意识摸手机想要查看日历,疑心他是不是穿越了,这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同样的事还能演上第二回?
可当他看到日历显示如今确实是2023年后又不怎么高兴地撇嘴,满脸的不高兴。
应春和的举动尽数落在任惟眼中,可爱得令他忍不住发笑,轻易就驱散了方才那通电话带来的郁气。
“任惟,你笑什么?”应春和有些恼,瞪向他。
任惟轻咳一声:“看到你这么舍不得我,我很高兴。”
应春和一哽:“谁舍不得……”
任惟微笑补充:“而且好可爱。”
应春和:“……”
任惟的话说得直白又坦荡,好似并无半点调笑的意思,偏偏应春和却听得面红耳赤,热意汹涌。
任惟正了正色,补充了一点电话里没说的:“我爷爷这两年身体每况愈下,这次进医院估计情况不会太好。”
对于任惟的爷爷,应春和不曾蒙面,唯一的了解都来自于任惟之口以及一些网络上能够查到的信息。
他到底不是圣母,做不到在明知促使任惟与自己分开的力量中也有其爷爷一份,仍对人爱屋及乌。只不过,在病痛与生死之前,过往的一切恩怨变得没那么重要。
应春和到底流露出些微的关切,劝慰任惟:“别太担心,会好的。”
任惟对他笑了下:“我不担心,担心也没什么用,我也不是医生,做不了什么。”
任惟进了房间整理行李,应春和想要帮忙,任惟却没让,只好在旁边干看着。
看了一会儿,应春和突然发现任惟带的东西是不是太少了,出声提醒:“你衣柜里的衣服怎么不放进去?不一起带走吗?”
任惟抬起眼看过来,有些无奈地道:“我还会回来,干嘛都带走?”
“噢。”应春和干巴巴地应了一声,意识到自己确实问了个蠢问题,倒显得自己好像催着人走似的。
也是巧了,今天刚好有轮渡,任惟便将船票和航班都订好了,下午就走。
“这次我可能会去比较久,如果我爷爷真的没医治过来,短时间我应该没法抽身。”任家里,任惟这一辈中他最年长,能力也有目共睹,若任老爷子过世,理应轮到他去操办葬礼,自然会有的忙。
思及此,任惟颇有些头疼地揉了揉眉心,继续对应春和说道:“回去之后应该会比较忙,你给我打电话恐怕不是都能接,要是有什么事就给我发信息,等我空下来了就会回你。”
应春和觉得自己应当是不会有什么大事一定要给任惟打电话的,他这操心得未免有些多余,可是他看着任惟眉宇间难掩的忧虑和担心到底没有吐槽,乖乖点了点头。
殊不知应春和这副乖巧懵懂的神情令任惟徒增许多不舍,心里也跟着痒痒的,翻翻找找,把自己带来的唯一一件饰物,聚会那天戴过的银色胸针拿了出来。
他郑重其事地把那枚胸针放在应春和的掌心里,略微歉意地承诺:“抱歉,我现在就只有这么个东西,你先将就收下,之后我再用别的来跟你交换。”
应春和垂眼看向手心里的银色的松叶胸针,心道任惟好狡猾,留下这么个东西想要时不时扎他一下,好叫他时时想念,常常惦记。
还附带这么一句似是而非的承诺,心机颇深。
应春和抬了抬下颌,看起来很勉强地把那枚胸针给收下了。
任惟往他跟前凑了凑,讨好似的又附赠一个吻,送完之后自己意犹未尽地舔舔唇,很快大方地再送上第二个、第三个吻。
应春和被他吻得头晕脑胀,模模糊糊地想起“吻别”这个词,亲吻着告别,绵密黏稠的亲吻消解了原本离别的苦痛与不舍。
他想,这或许也是任惟的意图所在。
上飞机后,任惟短暂地睡了一觉,做了个梦,是他在美国时常会做的梦,只是这次他清晰地看见了应春和的脸。他看清了应春和脸红,应春和生气,应春和冷脸,每个神情都那么生动,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睁开眼时,飞机刚好落地北京,任惟不舍地从温暖的梦中抽离出来,神情淡漠地下了飞机,找到来接他的助理,上车直接去了医院。
任惟抵达医院时,任家的人都已经到齐了,一个不落地出现在icu门口,比平时家宴都还要来得齐,但这些人中究竟有几个人是真的担心任老爷子的身体,任惟不得而知。
任惟用冷淡的目光一一扫过众人,挨个打了招呼,只有小姑任芸和母亲陶碧莹回应了他,其他基本当作没听见。
任惟也不介意,开门见山道:“我来医院之前,何律师给我打了通电话。”
何律师是跟了任治诚多年的律师,家里的人基本对他都不陌生。
此言一出,众人的目光都纷纷投了过来,其中任惟的小叔任楷最为迫切,急得问出了声:“何律师说什么?”
任楷平日里并非是这般沉不住气的人,任惟对于自己这个小叔的印象其实并不深,因为他行事低调,沉稳内敛,多年来都甘居于他父亲仁恒之下,仿佛任劳任怨,不争不抢。
但事到如今,任楷似乎觉得自己已经没了装的必要,迫不及待地露出了马脚来。
任惟笑了笑,比之众人的急切显得格外从容不迫:“何律说,如果我爷爷去世,让我联系他,他会过来宣读遗嘱。”
见任惟说出了遗嘱二字,任芸也不再淡定,眉头紧锁:“小惟,但是何律为什么要联系你呢?这不合规矩。”
是了,若是任惟也是遗产继承人之一,何律不该在宣读遗嘱之前联系任惟,但这毕竟是老爷子任治诚的要求,也是任治诚给遗嘱上的一层保险。
任惟淡淡一哂:“因为遗嘱一共有两份,一份是对房产和现金的分配,一份是对公司股权的分配,前一份会在病房里宣读,后一份会在葬礼上宣读。”
说到这,任惟稍作停顿,将最重要的一点也抛了出来:“不过,主要还是因为我放弃了公司股权的继承。”
“任惟,你说什么?!”反应最大的自然是任惟的父亲仁恒,他对此一无所知。
如今他已经年近六十,快到了从公司退下来的年纪,在他看来等他退下来之后,这公司自然就要落到任惟的手里。
纵然他看自己这个儿子有诸多不满,纵然老爷子也有几分微词,但任惟的能力毋庸置疑,凭他能不依靠家里在外闯出一番天地这点,就足以甩家里这些酒囊饭袋几条街。
可是现在任惟居然说什么放弃继承,开的什么玩笑?这是他说放弃就可以放弃的吗?
只是任恒这番剧烈的心理活动与不小的反应都只换来任惟淡淡的一个眼神,那眼神里没有丝毫歉意,更没有丝毫温情,不像在看自己的父亲,倒像在看一个疏离陌生的合作商。
“遗嘱已经拟好了。”任惟只是这么说,告诉任恒一切都已尘埃落定,没有再转圜的余地。
任恒身形一晃,目露震惊,这才知道他当年自以为是给儿子上的一课何其愚蠢,不仅断了他们的父子情分,也结下了恶果。他的儿子随他,睚眦必报,如今羽翼已丰,自然要向当年施恶之人一一讨还。
光是这么想着,他的后背就泛起了阵阵寒意。
任惟不再看他们任何一个人,似乎懒得多给谁一个眼神,自顾自地去了吸烟处抽烟,留下众人提心吊胆地等在原地。
第88章 “真的都问心无愧吗”
抽烟与喝酒都是成瘾性极高的事,任惟很早以前便都一一学会,不过目前为止都未曾对其中任一染上瘾。
贺奇林等一众友人将此归结为任惟自律性太强,任恒则将此归结为他教导有方,但任惟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与他个人的自控能力、家庭的规训作用都无关,当然也并非是出于侥幸。
真实的原因其实再简单不过——抽烟也好、喝酒也罢,这两件事本身都令任惟兴致缺缺。
初尝酒味,任惟十三岁。
那天家里的佣人都放了假,父母俱不在家,他一个人摸进地下酒窖,出于好奇挑了一瓶外观漂亮的酒想浅尝一口,却不知不觉喝了个干净。
时至今日他也不知那瓶酒的具体度数,只记得喝下去没多久身体便渐渐生出热意,喉咙也有轻微的灼烧感,除此之外再无旁的感受。
即使他离开酒窖回到房间后便倒头睡去,次日醒来形容潦草,手中还抱着个空酒瓶,心里也不以为意,更不认为那是醉酒行为。
当然,他的确由此得出自己天生酒量不错且喝酒不会上脸的结论,这也成为他日后在应酬桌上谈下一单单合作的独家技巧,令许多人不得不叹服。
初尝烟味,任惟十五岁。
给他递烟的是一名体育生,与他的交情马马虎虎,递的时候估计以为他不会接只是想意思一下,但那天他自己也不知是何种心情作祟,竟鬼使神差地接了过来。
常人都说抽第一口烟很容易被呛到,任惟却是例外。尽管他吞云吐雾的动作稍显生涩,但就神情来看并无太多不适,散漫又从容,好似早已熟稔。
那根烟最后被他摁灭在身侧的一颗树上,随着他的动作,残存红星的一截烟蒂陷进树干的沟壑里,苍白色烟灰簌簌抖落,他人生的第一根烟就此燃尽。
简而言之,这两件事并没能让任惟产生任何类似于愉悦、兴奋、刺激的感受,甚至也不具有任何挑战性。
而这世上的其他事物也大多如此,之于任惟都太唾手可得,诸如金钱、名利、权力,所以都不可贵,都不稀罕。
如果将世界比作一个巨大的游乐场,那么任惟就是通过贵宾通道提早进入游乐场,并早早玩遍所有游戏项目的顾客。整个游乐场也像是被一张巨大的灰白色防尘布笼罩,令本该充斥欢笑声的多彩乐园化为黑白的默剧。因此,旁人期盼已久,排了长队才进入的欢乐场所对任惟而言则枯燥无味。
直到他看到唯一一抹彩色。
那彩色并非出现在游乐场里的任何一个游戏项目里,而是出现在最寻常不过的地砖上,随着一个人一蹦一跳地跃过,灰暗的地砖显出斑斓的色彩,犹如七彩的琴键被一一奏响,连成一支欢乐的乐曲于任惟的耳畔奏响。
任惟的目光移到那人的脸上,发现他们有过一面之缘,在不久之前的迎新典礼上。
他叫什么来着?应……
“应春和,至若春和景明的春和。”心底有道清冽的声音替他回答了。
原本灰白的世界从那天开始渐渐染上色彩:
应春和的眼睛是偏褐色,在阳光下会显出宝石般晶莹的色泽;应春和的皮肤是小麦色,如同面包店鲜烤出炉的小面包般柔韧;应春和的耳垂是淡粉色,跟他的距离越近粉色就会越深……
“好几个老师都说我的色感很好。”应春和说这话的时候很谦逊,垂着眼睫,唯有唇角微翘,泄露一丝年轻人的自得。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